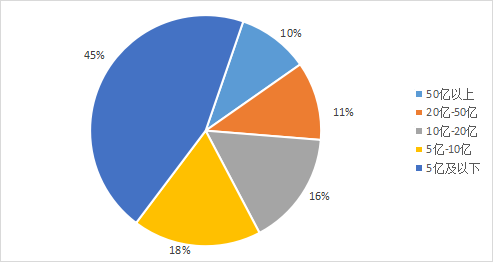春寒料峭,高原阳光却异常灼人,已过花甲之年的尕查站在几成沙地的草场,望着刚一露头就被老鼠啃掉的草芽,心痛不止。 尕查曾是位于三江源核心区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昌麻河乡血麻村的村支书,2004年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的“生态移民”搬迁到了260公里以外的大武镇移民点。他告诉本刊记者,8年来,他每年都会回家乡看看,如今大片禁牧草场被鼠兔破坏、沙砾遍地,不少河流已经干涸了。
“全球变暖冰先知”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包括青海玉树、果洛、黄南等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众多著名江河的发源地,每年向中下游供水600多亿立方米,养育了超过6亿人口,被誉为“中华水塔”、“亚洲水塔”。
资料记载,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境内的阿尼玛卿山,主峰海拔6282米,过去分布着80多条大小不一的冰川,是为黄河源头提供水量最多的雪山。 “一项监测显示,近些年阿尼玛卿山冰川退化明显加快,边缘部分厚度非常稀薄。有时坐在西宁至玉树的飞机上看到阿尼玛卿山,我就担心也许10年后或者更长的时间,这里的冰川可能会永久性消失。”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负责人不无忧虑地说。来源:瞭望观察网 位于高原腹地、三江源地区的雪山、冰川,总面积近2400平方公里,冰川资源蕴藏量达2000亿立方米,是除西藏和新疆之外冰川覆盖面积最大的地区。据估算,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冰川融水补给比重分别达到18.5%、1.3%和6.6%。 青海省测绘局高级工程师成海宁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三江源区冰川变化,他们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长江源区冰川面积1968--1971年时为1283.66平方公里,到1999--2002年间为1215.53平方公里,近30年间总体萎缩了5.3%。统计表明,长江源区计有756条冰川,绝大部分冰川表现为后退,只有极少部分冰川处于前进状态,其中有两条小冰川已经彻底消失。 成海宁说,长江源区最大的冰川——色的日冰川面积变化率最大,近30年间面积减少了12.9%。自1966年以来,黄河源区的冰川退缩比例最大达到77%。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效存德说,“全球变暖冰先知,多年的观测研究显示,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地区85%至90%的冰川都在退缩。” 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水文分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辛元红分析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三江源地区冰川雪山持续消融减退,冻土层解冻加速,沼泽湿地减少,在短期内造成河流、湖泊水位有了大幅度上涨。但从长远看,这将改变三江源水系分布格局,甚至使源区水源濒临枯竭、荒漠化加剧,进一步的后果是整个江河流域出现干旱。
千疮百孔的草原 “草原禁牧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鼠害。”位于三江源核心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常务副县长才多杰告诉记者,治多县共有可利用草场2800万亩,其中700多万亩鼠害严重。据介绍,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治理了几十万亩,但只占全县鼠害面积的一小部分。加之害鼠繁殖快,往往是当年灭了,过两三年又复发泛滥了。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玛查里镇的草场海拔相对较高,牧草长得稀稀拉拉,46岁的藏族牧民诺多对记者说:“我家近8000亩草场,你看到处是鼠洞,牧草长得差、不够吃,我们想尽办法买草,每天喂100多斤饲料,但470只绵羊还是瘦得厉害。”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治多、杂多以及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泽库等县的草原上,鼠害严重,一些地区几乎寸草不生、土壤裸露,甚至出现“鼠进人退”现象,逼得牧民只得一年四季走圈放牧。 “目前,全省草原鼠害面积达1.2亿亩左右,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危害的重点区域就是三江源地区。”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调研员石德军说。 据专家介绍,高原鼠兔、高原鼢鼠以及高原田鼠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牧草,而且其啃食、掘洞、堆土等活动加速了草场退化、地表裸露,导致黑土滩出现,黑土滩再经过自然风化,最终变成沙漠、荒漠。 本刊记者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和日乡采访时也看到,一垄垄黄沙在大风吹拂下,不断增高加厚,侵袭着牧民草场。黄南州三江源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说:“这里大约有20万亩沙化土地,多年来未进行治理,正不断扩张、蔓延。”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认为,三江源地区是独特的高寒草原生态系统,对维护“中华水塔”安全意义重大。他告诉记者,通过遥感监测和模型分析,2005年至2011年三江源区植被指数93.1%没有变化,同时有5%变好,但还有1.9%变差。
“唯一的技能就是放牧” 为实施保护三江源的工程项目,先后有5万名藏族牧民搬离生态脆弱区,开始集中居住。2004年,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生态移民”,与尕查一样,南加与162户群众一起搬迁到了州府所在地大武镇沁源新村。 尽管搬迁后住房、医疗、就学等条件有所改善,但对于世代“逐水草而居”的广大搬迁牧民来说,“生态移民”的身份,使他们朝夕之间成为非农、非牧也非城镇居民的特殊社会群体,面临严重的生计难题和发展困境。 南加告诉记者,由于禁牧减畜,他将原有的70头牛、120只羊全部出售,如今卖牲畜的“老本”早花光了,除去领取国家一定粮食和生活补助外,他家最大的生计仍在草原上:挖虫草、帮牧。 “挖虫草完全靠天吃饭,不牢靠。但我家几辈子都是牧民,唯一的技能就是放牧,也没有其他法子。”南加说,除了挖虫草,他与妻子到其他乡镇给以草定畜户帮牧,干几月下来,人家不过在年底给点酥油和曲拉。 “现在的生活不如草原上好。过去我们家有100多头牛、300多只羊、7万亩草场,吃肉、喝奶、用燃料不花钱,一家人的生活不用愁。”同住在大武镇河源新村的搬迁牧民、62岁的给青很怀念草原上的生活。他说,这几年一家10口人主要靠政府发放的饲料粮补助、燃料补助以及生活困难补助过日子,而所有这些钱加起来还不足2头牛的价钱。 果洛州玛沁县三江源办公室主任尹东曲说,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生态移民”收入仅有城镇居民的20%左右,很难在城镇站住脚。有的移民买了些牲畜过起游牧生活,牛羊吃到哪里,人就跟到哪里,甚至到了川藏草场上。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杜发春调研后说,搬迁移民中70%的人员就业没渠道、发展没门路,生活变得日益艰难,移民村正在变成“低保村”、“贫民窟”。 在青海省发改委生态移民组负责人师延俊看来,“生态移民”进城后收入少了,生活成本却大幅增加,生活质量无法保障。“尽管政府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并不理想。”据统计,2011年三江源生态移民人均纯收入为2350元,大部分生活在国家新的扶贫线以下。记者 何伟